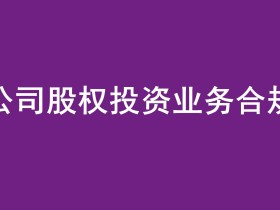前言
在我們對賭回購系列之二《對賭回購主體怎么選?法律限制+履約能力雙維度拆解》一文中,我們探討了對賭協議所涉股權回購主體的選擇問題。基于《公司法》和《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紀要”)的規定,與標的公司對賭存在法律限制和操作上的不確定性,而與創始股東對賭則合法有效、易于操作,但對創始股東的誠信度和償付能力要求較高。在投融資實踐中,投資人為保護自身權益,傾向于優先選擇要求創始股東作為股權回購主體。然而,創始股東通常與標的公司的利益深度綁定,不僅將個人或家庭大部分甚至全部資金用于公司經營,甚至以個人或家庭房產抵押擔保貸款以支持公司運營,其個人職業發展、家庭生活亦與公司運營密切相關。若要求創始股東承擔無限額或高額回購責任,可能導致創始股東傾家蕩產,甚至影響其家庭基本生活。有些創始股東因而“破罐破摔”,“積極”逃避債務、“消極”經營公司,最終反而損害投資人的利益。正是在“定向減資難操作”與“創始股東無力擔責”的雙重困境下,“以創始股東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為限承擔回購責任”成為投融資雙方博弈后達成的平衡方案。本文將結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判例,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以股權為限”的法律效力與商業邏輯
對賭協議作為投融資雙方自愿達成的契約,只要其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就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按照協議約定來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對此,九民紀要也予以肯定。以股權為限的約定,是對創始股東承擔回購義務設置的責任限制,也是投融資雙方對各自風險和收益的一種合理安排,并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亦屬合法有效。
在商業實踐層面,這一安排既回避了《公司法》和九民紀要關于定向減資的規制要求,又兼顧了投融資雙方的核心利益訴求:從投資人角度看,雖未獲得現金回購的“剛性保障”,但相較于完全放棄回購權利,以股權為限的約定至少為其提供了一定的“兜底保障”,避免投資完全“打水漂”;同時,該約定也倒逼創始股東努力實現對賭目標,避免觸發股權回購,即使未能實現對賭目標,在其盡心盡力經營下,公司估值如果沒有因客觀因素大幅縮水,創始股東所持股權價值較高,無論以何種方式變現,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投資人的回購權的實現,實際上間接維護了投資人的利益。從創始股東角度看,這一安排有效規避了創始股東因履行回購義務而導致傾家蕩產的風險,緩解了其個人及家庭的顧慮,相當于一顆“定心丸”,從而令其能夠更積極地投入公司經營,為標的公司的持續發展保留了核心動力。
從投融資雙方博弈達成的共識不難看出,雙方真實的意思是創始股東需要承擔股權回購義務,但以其所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為責任上限。換言之,一旦對賭失敗,創始股東面臨的最高責任便是將其所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全部變現,用于向投資人支付股權回購款。如果無法順利變現,則將其所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全部無償轉讓給投資人以“折價抵償”投資人的股權回購款。無論如何,對創始股東而言,這已經是最壞的結果,無需以其個人的其他財產承擔回購責任。
然而,在商業實踐中,由于很多對賭條款中只是約定“以股權為限或者以股權價值為限”,沒有具體明確的操作約定,在股權回購觸發后,投資人會對“以股權為限或者以股權價值為限”這種粗略的約定作出種種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解釋,并導致爭議。
二、主要爭議事項與混亂的裁判觀點、執行口徑
如前文所述,約定以創始股東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或股權價值為限進行回購,在商業實踐中已引發諸多爭議。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創始股東的回購責任是否僅以其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為限,如果該等股權的價值不足以支付回購價款,是否應當以其個人的其他財產承擔回購責任?二是如何確定創始股東持有的股權的價值?
1、 創始股東的回購責任是否僅以其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為限?
如前所述,從商業邏輯角度看,投融資雙方簽訂協議時經博弈達成的共識,顯然是創始股東的回購責任僅以其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為限,除非創始股東存在協議約定的惡意行為或者明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其不應當以其個人的其他財產承擔回購責任。
然而,一旦觸發回購,投融資雙方又未能理性協商,如果相關協議對此沒有明確約定,且并無其它證據證明上述投融資雙方達成的默示共識,則創始股東的回購責任是否僅以其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為限便會成為爭議焦點。以股權這個特定“物”為限便很容易擴張解釋為以“股權價值”為限,一旦這個解釋被采納,股權價值便成了確定創始股東回購責任的“金額”標準,而金額確定后,創始股東的回購責任自然就不再限于其所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還包括其銀行存款、房產、車輛、股票、其他公司股權等等任何屬于個人的財產。
在上海市崇明區人民法院(2019)滬 0151 民初 8768 號某資產管理中心與張某、吳某等股權轉讓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中,判項中僅列明以“直接或間接所持股權價值為限”支付股權回購款,在該案進入執行階段后,上海市崇明區人民法院(2020)滬 0151 執 4407 號執行裁定書將執行范圍擴大到了創始股東的全部財產,凍結了其名下銀行賬戶、車輛、房屋等財產。事實上,在此類執行案件中,執行法官執行的是被執行人的金錢給付義務,只要裁判文書沒有列明“以拍賣、變賣創始股東直接或間接所持股權所得的價款為限”,執行法官就難免會將執行標的擴展到創始股東的其他個人財產。
2、 如何確定創始股東持有的股權的價值?
在司法實踐中,對這一爭議焦點主要有以下幾種認定標準和裁判思路:
(1)根據協議約定的股權回購價款并參照創始股東所持股權比例來確定“股權價值”
在(2020)浙01民終3422號浙江某股權投資有限公司與俞某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案涉股權目前的市場價值極低,若僅以創始股東實際持有股權份額在執行階段的評估拍賣價款為限承擔責任,顯失公平。故以當事人各方約定的股權贖回價款作為依據并參照創始股東受讓股權的比例確定相應股權償付價款。該裁判思路認為投融資雙方經博弈達成的共識“顯失公平”,顯然更注重對投資方利益的保護,但卻忽視了對賭的本質邏輯是“估值調整”,系投融資雙方在簽訂投資協議當時對目標公司未來發展的一種博弈,因此,投融資雙方均應承擔相應的經營、管理和市場風險。在沒有證據證明創始股東存在違約行為的情況下,如果僅因前述風險致使目標公司經營未達預期從而導致創始股東持有的股權價值嚴重低于回購金額,而要求創始股東以其個人財產承擔回購義務,相當于由創始股東承擔大部分商業風險,這對其而言才是“顯失公平”的。
(2)將目標公司在投資人該輪投資后的估值作為股權價值的認定依據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在2022年就寧波某股權投資中心與北京某科技公司之間的股權回購糾紛作出的仲裁裁決中指出,鑒于目標公司投后估值是案涉合同作價及對賭協議進行價格調整的基礎,林某等應以《增資協議》第2.1條約定的目標公司投后估值作為股權折算現金的計算基礎,來確定其承擔的股權回購責任限額。這種認定方法同樣背離了雙方簽訂對賭協議時約定“以股權為限”的初衷。首先,目標公司在投資人該輪投資后的估值是確定的數值,如果這是投融資雙方的初衷,直接約定創始股東的責任上限的數值即可,無需多此一舉再約定“以股權為限”。其次,通常創始股東持股比例遠高于投資人,以投資人該輪投資后的估值來確定創始股東承擔股權回購的責任限額,創始股東所持股權價值自然遠高于投資人的投資款,同樣使得約定“以股權為限”純屬多此一舉。第三,目標公司的估值實質上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以投資時的估值來認定股權價值,與對賭的實質——估值調整的邏輯背道而馳。
(3)其他可能的認定標準
除了上述認定標準外,司法實踐中還可能采用前輪融資估值、創始股東履約時的“變現價值”、執行時拍賣或變賣的價值、回購條件成就時或者投資人主張時或者司法裁判時的目標公司估值等標準來確定股權價值。
顯然,不同的法院/仲裁機構的裁判觀點千差萬別,這導致在不同的案件中,同樣的對賭股權回購條款可能會有不同的裁判結果,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仲裁風險和不確定性,也影響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不僅如此,執行口徑也同樣無法統一。在司法實踐中,審理階段對“創始股東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價值”作出具體量化的案例較少。在較多的案例中,司法機構往往僅簡單判決“以創始股東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價值為限”承擔責任,而不對該股權價值進行具體確認。這就導致進入執行階段后,執行法院難以判斷執行標的,各地法院的執行口徑因而無法統一。例如,股權價值可能會受到市場波動、公司經營狀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執行時難以確定一個準確的數值。在一些案例中,由于股權價值難以確定,執行法院甚至會作出“暫不具備繼續執行條件而終結本次執行”的裁定,使得投資方的權益無法得到有效實現。例如,在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2019)津 0116 民初 6075 號某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張某、吳某合同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中,判項中列明以“直接或間接所持股權價值為限”支付股權回購款。在該案進入執行階段后,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2020)津0116執12545號執行裁定書認為,由于依照本案執行依據的判決書陳述內容,現尚無法確定其他被執行人應承擔的責任金額,本案暫不具備繼續執行條件,申請執行人同意本案終結本次執行階段。而在上海市崇明區人民法院(2019)滬0151民初8768號某資產管理中心與張某、吳某等股權轉讓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中,判項中同樣僅列明以“直接或間接所持股權價值為限”支付股權回購款,在該案進入執行階段后,上海市崇明區人民法院(2020)滬0151執4407號執行裁定書將執行范圍擴大到了創始股東的全部財產,凍結了其名下銀行賬戶、車輛、房屋等財產。這兩個案例表明,在審理階段不明確股權價值的具體量化標準,不僅會給執行帶來很大的困難,而且不同地區的執行法院可能會采取不同的執行方式,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
三、我們的建議
為了有效應對上述挑戰和不確定性,完善對賭股權回購中以創始股東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為限的相關法律制度和實踐操作,楊春寶律師團隊擬提出以下建議:
1、建議完善對賭股權回購條款設計
投資方和創始股東在簽訂對賭協議時,應更加謹慎地設計股權回購條款,如果雙方均確認創始股東以股權為限承擔回購責任,就應當在協議中明確股權價值的確定方式,股權變現的條件、期限、方式等,以及股權無法變現時的處理方式,并明確創始股東不以其個人的其他財產承擔回購責任以及相關例外約定。關于股權變現的方式,除了向第三方轉讓、向投資人“折價抵償”外,還可以引入領售權條款。參考當年轟動大江南北的“俏江南”案,鼎暉資本在投資協議中約定了回購權、領售權和優先清算權連環機制,一旦對賭義務人張蘭未能如約履行股權回購義務,鼎暉資本有權啟動領售權,要求張蘭與鼎暉資本一起“賣”,并進而行使優先清算權,因而,確保了創始股東所持股權可以變現。最終,因俏江南未能如期上市觸發回購事件,且彼時張蘭亦無力回購,故最終鼎暉資本通過行使領售權實現退出,并根據優先清算權實現了約定的投資收益。
2、建議統一裁判尺度
如前所述,在商業實踐中,因協議約定不明導致的爭議越來越多,而裁判與執行思路的混亂也導致很大的不確定性,無法形成合理預期。建議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或者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召開研討會等方式,加強對各級法院在對賭股權回購案件裁判中的指導,統一裁判尺度,提高司法裁判的質量和公信力。統一的裁判尺度應當回歸商業邏輯,在對賭股權回購案件中,如果協議約定創始股東以股權為限或股權價值為限承擔回購責任,除非協議另有約定,股權價值應以投融資雙方協商一致的方式確定,如果無法協商一致,則應委托專業的評估機構予以評估,并以拍賣或變賣方式處置創始股東所持股權。創始股東支付回購款的責任僅以其所持股權處置價款為限,不應執行其個人的其他財產。
結語
如何認定以創始股東持有的標的公司股權為限的回購責任,不僅關乎投資方與創始股東之間的利益平衡,還涉及到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適用的統一性等多方面的問題。糾紛的產生根本上源于協議約定不清晰、不明確,另一方面,一些裁判機構對投融資雙方形成“以股權為限”共識的背景與商業邏輯缺乏準確的認知,因而采納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因此,無論在融資協議簽訂環節,還是股權回購訴訟或仲裁環節,均需專業股權投資律師的幫助。楊春寶律師團隊將持續關注相關的商業案例和司法判例,并在第一時間作出解讀。